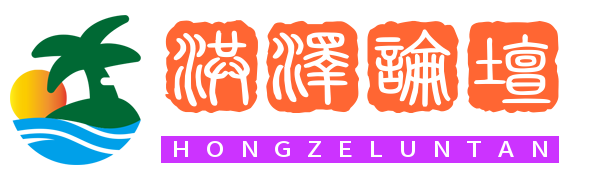素有“清初学人第一”之称的纳兰性德一生笔耕不戳,他的《饮水词》(原名《侧帽集》),“井水吃处,无不争唱”。
在妻卢氏病故后,他写了大量的悼亡之作追忆以往欢愉、悼念早逝亡妻,其数量之大,在悼亡诗词史上实属罕见。
纳兰性德在继承古人悼亡诗词精髓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他的悼亡词情深意切、至真至浓、灵动细腻、撼动人心,是花与惜花人的对话,是对生死天堑的跨越。
尤其令人称赏的是,他的悼亡词悲郁中飘过缕缕自然清新,开悼亡词一代清丽词风。
观纳兰性德之词,至真至诚,至情至浓,字字句句,发乎内心,少泥淖拖沓之语。
王国维称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1]纳兰之词,素以清丽素雅著称。
其边塞作,虽有豪放之句,而豪放中常有清秀之笔,如春潮过塞外,三分豪放情,七分清丽语。
其友情诗,多为忠义句,又不少婉约之情。
占其词作最多的爱情作品,清新之气弥漫字句之间,染出一抹自然之色。
而笔者独爱容若悼亡作。
笔者在这里论及的悼亡词,专指纳兰性德悼卢氏之作,即自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677年6月29日)始,至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其病故十余年间所做的怀念、悼亡亡妻卢蕊之作。
纳兰性德悼亡词的特点之一,在于他的悼亡词是一种对话,是生者与逝者的心灵沟通。
观此前悼亡之作,悲情深切,字里行间悲悼之情溢满,已是悼亡诗词的上乘之作,但还是少了一点灵犀之美。
譬如说,《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
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男子手抚绿衣哭泣,这是类似于自言自语式的悲悼,不乏真情,但少了些许天人间的通灵。
又如潘岳者,《悼亡诗》情深意切,“如彼翰林鸟,双萋一朝只。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若无悲情,难成此句。
“抚衿长叹息,不觉泪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令读者每每读起,也不由得泪沾青衿,这算是凄。
若是悲切中再多几分灵动的美,就是凄美绝佳的上品了。
纳兰性德的悼亡词,载情为本,张显灵性,悲凄中荡漾着渴望心灵沟通的灵动之美,脱去了干涩的悲伤,换之以灵犀暗度,不仅感染读者的感情,也撼动着读者的灵魂。
纳兰性德《南乡子·为亡妇题照》: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
盈盈。
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
午夜鹣鹣梦早醒。
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
泣尽风檐夜雨铃。
在这首词中,纳兰不是“哭”老婆,也不是“哭”自己,更不是自言自语,他在试图通过这种提照的方式来沟通生死,与亡灵产生共鸣。
天人永隔,因“只向从前悔薄情”,便通过“凭仗丹青重省识”这种方式,再来认识亡妻,回忆往事。
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亡妻一样,也能够对自己“重识省”,但终落个“一片伤心画不成”。
“画不成”是因为天人相隔沟通失败。
但纳兰性德并不放弃这种沟通,而是始终相信爱可以穿越生死,产生感应。
后半阙提到“卿自早醒侬自梦”和“夜雨铃”。
逝去的人解脱了,活着的人却陷在梦里。
“夜雨铃”应取典于唐明皇与杨玉环之事。
相似的,在《浣溪沙(风髻抛残秋草生)》中,也提到了唐明皇与杨玉环七夕盟誓和“雨淋铃”。
传说唐明皇与杨玉环生死相隔,但依然能通过使者,在海上仙山寻到了太真。
纳兰也希望能与亡妻产生这样的天人沟通,“信天上人间非幻(《鹊桥仙·七夕》)”,并用了各种方式,“凭仗丹青重省识(《南乡子·为亡妇题照》)”是一种,“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虞美人(春情只到梨花薄)》)”又是一种,“重泉若有双鱼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也是一种,但这些方法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但是“丁巳重阳前三日(《沁园春》)”这天,纳兰性德成功了。
在这首《沁园春》全词开始之前,有一段序,如下: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装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
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
”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
《沁园春》是一首记梦词,其中的一往情深、缠绵悱恻可与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相媲美。
亡妻所衔之恨也正是纳兰性德所含之怨,既然人已无法团圆,就化为一轮冰月,纵有阴缺,犹有圆时。
古人悼亡或是独自垂泪,或是相顾不语,纳兰性德不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而是得到了亡妻的“呼应”。
虽然这种对话无法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但却是纳兰性德悼亡词追求心灵沟通的有力证明。
纳兰性德悼亡词是惜花人与花的“对话”。
以悼亡词的词性来看,花应是逝者,惜花人应是生者,也就是说,卢蕊是花,纳兰容若是惜花人。
卢氏名蕊,名字就透着花香气,说她是花,合乎情理。
“一宵冷雨葬名花(《山花子(林下荒台道韫家)》)”,“趁星前月下,魂在梨花(《沁园春·代悼亡》)”,都把卢蕊比作花朵。
纳兰性德深爱卢蕊,说他是惜花人,同样合乎情理,纵然“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可这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词作,字字惜花,句句怜花,不是怜花句又是什么?这一笔“口是心非”,却更显惜花人的多情。
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这些悼亡词时,便会发现这样一个奇妙的现象,很多时候,这种惜花人与花的角色是相融和互换的,纳兰性德站在了花的位置上,卢蕊站在了惜花人的位置上。
一句“惜花人去花无主(《蝶恋花(萧瑟兰成看老去)》)”,巧妙地把惜花人与花的角色反串,不再追求单方面的怜惜,而是升华了双向的爱怜。
在这样的惜花人与花的对话中,谁是花,谁是惜花人已经不重要了,甚至连惜花人与花存在与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一份真情在彼此的心里激荡过,并且跨越了生死的界限,永远燃烧着。
纳兰性德开悼亡诗词的清丽之风。
元稹著名的悼亡词《离思》“曾经仓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表现了爱情无法逾越生死的悲情苦楚和作者的满腹愁肠。
沧海与巫山之句堪称经典。
史达祖的悼亡词《忆瑶姬·骑省之悼也》同样是悲从中来,无可断绝。
这些诗词都是心灵的咏叹,是作者血泪的交织和情感的喷涌。
如果说,在纳兰性德之前,悼亡诗词是以悲情为主,那么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在继承了悼亡诗词情真意切、肝肠寸断的特点之余,又给悼亡诗词这种以沉郁、悲恸为主要基调的文学作品添以清新之色。
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在悲怆中透着徐徐清丽之风,与“其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2]不无关系,而悼亡意向的捕捉对此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纵观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作,梨花与月的运用,给其次作品增加了纯净的色泽,对于纳兰性德悼亡词风的独树一帜有着较大的影响。
在我所论及的纳兰性德悼亡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梨花、月等意向。
其中,月出现了19次,梨花、葬花、花、芳、香等出现了29次。
梨花与月在悼亡词的诗词史上都被使用过,比如说苏轼的两首悼亡词分别涉及到了梨花与月。
在其著名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出现了月。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在其《西江月》中出现了梨花。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以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这两首词分别是为了悼亡其妻子和其爱妾朝云。
梨花与月在纳兰性德悼亡词中高频率出现并非偶然。
这些意象都是纳兰性德与卢蕊的生活景观。
在卢氏生前,他与卢氏时常在回廊之上,梨花之旁,冷月之下,煮水泼茶,谈心论事,因此才有了《蝶恋花(谁念西风独自凉)》中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
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一个纵向与横向相交错的情境,不仅记录着过去今朝,也预见了悲寥的未来;不仅是思绪的聚焦,也是情感的辐射。
在这个情境中,主人公是容若和卢蕊,主题永远是爱和难以成全誓约。
在卢氏死后,这些情境便时常出现在他的词作中,使词情景交融,达到了“情即是景,景即是情”的境界。
不仅如此,梨花与月,都有着冰肌般的色泽,蕴含着淡淡的哀愁意味,用于词中,虽不及直呼生死、直呼惆怅来的淋漓尽致、直抒胸臆,却更有一番自然而纯净的滋味在心头。
在卢氏死后半个月时,纳兰性德写的第一首悼亡词《青衫湿遍·悼亡》中就出现了梨花。
上阙“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
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釭。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
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可见在卢氏生前,容若常与其漫步回廊中,相伴梨花影,因此在卢氏故后,容若才会发出“独伴梨花影”的悲悼和“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的真情叹惋。
至于月,因“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沁园春(丁巳重阳前三日)》)”,纳兰性德往往见月如人,情在月中。
一句“辛苦最怜天上月(《蝶恋花》)”,便将生离死别的无可奈何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成玦。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
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这是一种纯白干净的悼念,除去了累赘的悲伤和拖沓的抒情,只留得一汪冰月般的情意。
月是冷的,心却是热的,这样的一冷一热交融,便使翻腾的悲情退去了骇浪,也褪去了世俗的纷扰,平添了清潭般的深沉与宁静,趋向自然。
这种悼亡词的清丽既与其所运用的意向有关,也是他对亡妻情深至极的体现。
因为情深至极,反而不会刻意追求悲伤,只是让心中之情自然流淌,便足以感天动地。
《诗经·邶风·绿衣》中的男子抚衣追忆妻子的贤良,悲中内外还是悲。
又比如梅尧臣的《悼亡妻》:“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
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
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
”悲伤惆怅又岂是一个“愁”字了得。
这两首悼亡作都是真情的流露。
而纳兰性德的悼亡词的悲,更像是慰藉和寒暄。
《青衫湿遍悼亡》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
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釭。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
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
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
怕幽泉还为我神伤。
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
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人死心灭,活在世上的人才是最痛苦的。
在这样悲痛欲绝的时候,纳兰想的不是自己的孤寂悲寥,也不像古人,兀自悲切少了一个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人。
他想到的是已经撒手人寰、不知世间事的亡妻,怕亡妻在九泉下,“还为我神伤”。
不仅如此,还用了妻子的语气说:“道书生、簿命宜将息,再体耽,怨粉愁香”,相互慰藉之景仿佛就在眼前,更见两人素日的情深意长。
纳兰悼亡词的清丽之风正是源于这相互的怜惜。
徐志摩有一句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3]容若得卢蕊,算是幸,但终逃不过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