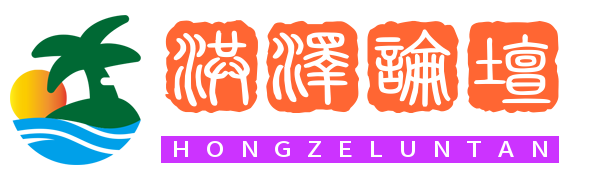古地图不仅是古代地理状况的反映,也是政治权力和地理观念的表达。清代历经康雍乾三朝,最终平定准噶尔汗国与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北,设置伊犁将军,实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全面管辖。在此期间,康熙帝和乾隆帝分别委派欧洲耶稣会士和清朝官员,采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测绘西域,并用经纬网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中的西域,表现了清代西域的现实情形,反映了元明以来西域蒙古化和突厥化的状况。雍正、乾隆年间,受清朝测绘的影响以及与俄罗斯和清朝征战、划界的需要,割据西域的蒙古准噶尔汗国也开始用托忒蒙文绘制《准噶尔汗国图》,反映准噶尔汗国以西域为中心的疆域观。从乾隆年间开始,除了清廷实测之图外,清朝官员和学者开始编绘《西域图志》等新疆图籍,这些图籍往往采用中国传统绘法并将清代地名与汉唐地名一并标注,突出新疆的台站体系和新建政区,表现清朝对新疆的军事控制和行政管辖。
一、清前中期的西域测绘与新疆构建
清前中期,由西方传教士领衔、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测量和桑逊投影法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系列舆图中,西域多绘注蒙古语和满语地名,而清朝官员和学者私人所绘的西域地图则基本保留汉唐西域地名。随着清代对西域统辖的强化,开始出现,而且清代地图中山川、政区和交通的表现精度也大为提高。
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之后,康熙帝就将全国疆域政区的测绘提上议事日程,并将其作为康熙中后期的施政重点。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年)间,康熙帝亲自主持,由西方耶稣会士白晋(Joach Bouvet)、雷孝思(Jean-Bapitiste R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e)、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rdoso)等率领中方测绘人员,用西方三角测量法实地测量经纬度,并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法绘制而成全国疆域政区总图《皇舆全览图》,至少有9种刻本和3种绘本传世,是18世纪以来欧洲绘制亚洲和中国地图的底图,在中国地图史和中外地图交流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描绘今东疆哈密简况的《哈密全图》是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一年(1711-1712年)间,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Jartoux)、法国耶稣会士潘如(Boujour)和奥地利耶稣会士费隐(Fridelli)率领中外人员测绘完成的,现有康熙分幅木刻版和彩色摹绘本两种单幅汉文本,以及康熙木刻和铜刻两种满汉文刻本传世。而描绘哈密地区的详图《哈密噶思图》与从吐鲁番到喀什地区的《杂旺阿尔布滩图》(即《策妄阿拉布坦图》),则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由费隐测绘而成的。两图分别绘注西域东部和中西部的山川、湖泊、城镇,图中的地名几乎全部是蒙古语和满语,而且与蒙元时代的蒙语地名多有不同,更标绘了许多以前地图中从未有过的小地名和新地名。两图第一次采用西方近代测量法和经纬网坐标系,较为翔实而准确地绘出了清代西域的现实地理情形,塑造了一个“西域”的地理形象。其铜刻拼接版中的西域地名全用满文标注,彰显了清前中期清人将西域视为关外、与中原汉地不同的地理观。
《雍正十排皇舆全图》是雍正三年(1725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结合新辟苗疆、改土归流、平定准噶尔、与俄国订立西北界约、改革政区的实际情况及海外舆图新资料补充修订而成的。其嘉峪关以西的西域部分全用满文注记,远达黑海与地中海一带,较《皇舆全览图》范围大为扩展,并更正、增加了一些地名,用虚线绘出了中原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道路,但因其采用西方投影测绘的经纬度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相结合的方格网坐标,使其误差较大。事实上,雍正朝与俄罗斯就中亚和西伯利亚都曾经进行过划界谈判,清廷完全掌握中亚和西伯利亚不少地方都沦为沙俄控制的事实,但却仍将其绘入《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之中。相较于康熙《皇舆全览图》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多了绘图技术上的中西调和取向、政治和疆域观念上的天朝一统思想。
《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基础上,于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755-1761年)增补西域、吐蕃新测绘的资料编绘而成的。该图范围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东至东海,比康熙《皇舆全览图》描绘的地理范围大一倍以上,是当时的亚洲全图,表现了清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一统”的疆域观。
乾隆年间的西域大测绘是在平定北疆准噶尔和南疆回部的背景下进行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部后,乾隆帝就指示群臣采用实地考察采访与文献考证结合的双重证据法来收集西域资料。其后乾隆又命何国宗、明安图、奴三、富德等人率西藏喇嘛及欧洲耶稣会士入疆测绘准噶尔地区,将其绘入《皇舆全图》,纳入清朝的疆域版图,彰显清朝天下一统的丰功伟业。乾隆年间的西域测绘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开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由何国宗总负责测绘,从巴里坤分南、北两路,北路由努三、明安图、傅作霖(Felixda Rocha)等负责,测绘天山北麓至伊犁地区;南路由何国宗、哈清阿、高慎思(Josephd’ Espinha)负责,测绘吐鲁番地区。这次测绘于当年十月结束;第二次主要测绘南疆、中亚,开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由明安图、德保、乌林泰及欧洲耶稣会士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Augustine Hallerstein)等人前往今新疆、中亚地区进行测绘。通过两次测绘,清政府获取了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南北两路广大地区90余处的经纬度数据,因此该图中西域部分地名的密度和准度都要高于《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图》。宋君荣(Antonius Goubil)又提供了中亚地区的地理资料,蒋友仁(Michel Benoist)综合上述数据和资料,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镌刻为“皇舆全图”铜版。在编绘《乾隆内府舆图》的同时,乾隆帝还命刘统勋、何国宗等人在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编绘《西域图志》,系统梳理西域历史地理,采用传统绘法编绘西域地图,体现了西域地图向传统的复归。
在全面掌控新疆的基础上,清廷在新疆建立起完善的台站体系和驻防体系,并陆续设置政区、营建城池。《乾隆内府舆图》在满语、蒙古语、突厥语林立的新疆地区突出标绘了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市)、景化城(今呼图壁县),伊犁地区的宁远城(今伊宁)、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镇)、绥定城(今霍城县水定镇)、惠宁城(今伊宁市巴彦岱镇)、瞻德城(今霍城县清水河镇)、广仁城(今霍城县芦草沟)、拱宸城(今霍城县西兵团第四师62团场驻地)、熙春城(今伊宁市西城盘子)等新建汉语城池,并用象形符号放大绘制了多方乾隆皇帝的御制碑,彰显了清王朝和乾隆帝开拓新疆的文治武功与教化“番夷”、镇抚边疆的政治雄心。在此,地图成为疆域的标志与权力的象征,乾隆帝通过地图语言表现了他“开拓万里回疆”、实现大清一统的文治武功。而且,从乾隆朝开始,“一统”或“万年一统”成为全国疆域图的主要名称。
二、准噶尔蒙古文《准噶尔汗国图》中的西域中心观
雄踞北疆的准噶尔汗国曾经是西域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在清朝西征和沙俄东进的背景下,准噶尔汗国国势日益穷蹙,最终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持续征讨下覆亡。在与清朝和沙俄交往、交战和边界交涉的过程中,准噶尔汗国受到清朝和沙俄的双重影响,开始用蒙古文绘制其疆域图。
在康熙晚期(约1713-1719年间)同清朝交战的过程中,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在今巴里坤或吐鲁番从清朝军队处缴获了两幅地图:第一幅是刻印版“切线与割线地图”;第二幅是绘本西域图,该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采用沿入疆主要道路两侧分别正向和倒置两种方向的“对景法”,用满文和藏文两种文字,绘注肃州至吐鲁番(也即今甘肃西部至新疆东部)一带的地理情形。准噶尔人用托忒蒙古文对后一幅图进行了翻译标注,全图共有地名536个。根据获取时间和地图形式推断,第一幅刻版图应该就是前文所述康熙五十七年刻印的《皇舆全览图》中的《杂旺阿尔布滩图》,第二幅图有可能就是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间,由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与理藩院主事胜住绘制的《甘肃新疆图》,或是在此基础上绘制的地图。将第二幅图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绘本《哈密全图》比较可以发现,两图中山脉、湖泊、泉源的绘法较为类似。
18世纪以来,沙俄不断东进南下,侵占准噶尔汗国领土,策妄阿拉布坦曾多次与沙俄进行交涉谈判。雍正七年(1729年)准噶尔珲台吉噶尔丹策零再次与俄国就疆界问题展开谈判,指责俄国侵占其北部领土。其后,噶尔丹策零便用托忒蒙古文绘制了《准噶尔汗国图》,表现其疆域边界,便于同沙俄交涉。1733年,此图连同准噶尔从清军处所获的两幅地图都被噶尔丹策零赏赐给了为他服务多年、行将回国的瑞典炮兵士官雷纳特(Johan Gustaf Lennart)。返回欧洲后,雷纳特对其中的两幅蒙古文地图进行了翻译和注记,其后瑞典、俄国学者也对两图进行了复制和研究。1743年雷纳特将三图及其他在准噶尔所获物品捐赠给了瑞典乌普萨拉皇家大学图书馆(Uppsala Universitetsbibliotek),噶尔丹策零所绘之蒙古文《准噶尔汗国图》被称为“雷纳特1号地图”,从清朝地图摹绘之蒙古文图被称为“雷纳特2号地图”。
《准噶尔汗国图》中的河流和湖泊的绘法受到清朝地图和沙俄地图的双重影响,但山脉的绘法较为独特。该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方位受中国传统地图的影响,绘制范围东起哈密,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撒马尔罕,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至楚河中游和塔拉斯,东北至喀尔喀界,西南至巴达克山,北疆注准噶尔人,南疆注于阗人,并注明周边其他族群。根据图中地名尤其是乌什吐鲁番中所反映的雍正九年至十年间清准战争后吐鲁番人迁徙情形,可以判断此图的绘制年代在1732年左右。
《准噶尔汗国图》是迄今所知唯一一幅由准噶尔汗国用托忒蒙文所绘制的准噶尔疆域图,其由噶尔丹策零绘制的形式也可能是受到康熙皇帝主持《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启发。该图直观描绘了18世纪中国新疆和中亚东部地区山川、湖泉、沙漠、城镇、族群的情形,生动反映了准噶尔汗国的疆域观和民族观,也表现了近代疆域领土观念在游牧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清中后期传统新疆图籍中的故土构建
康雍乾三大实测地图集的绘制、完善过程也是清王朝完成并巩固国家统一,明确清朝疆域界线,对边疆地区实行主权管辖的历史见证。然而,令人感慨的是,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与《乾隆内府舆图》在绘制完成后,一直深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除了皇帝个人欣赏使用和赐给少数朝臣和地方督抚外,并未能在中国社会推广使用,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和地理知识也未能在社会中普及并推动中国地图学整体迈向近代化。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所编《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官方图志及各地官修志书插图都未采用计里画方,更未采用经纬网,清朝前期实测地图中已经广泛运用的经纬网和投影技术被束之高阁。清朝中期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之时,主要运用中国传统形象绘法,采用以文献考据和制图综合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绘图方式,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的主流。
在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和回部并测绘新疆、建置政区的基础上,清朝中期的官员和学者纷纷绘制新疆图册,绘本和刻本新疆图籍大量出现,其体例和内容大多受到《西域图志》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新疆图籍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新疆图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西域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嘉庆《新疆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庆《西域舆图》,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嘉庆彩绘《伊犁总统图说》、道光彩绘《新疆全图》。这些单幅舆图或图册的涵盖范围大多东起甘肃嘉峪关,西到巴尔喀什湖,南起新疆与西藏交界,北到斋桑海(即今巴尔克什湖东北的斋桑泊),即清朝实际管辖的新疆,其内容重在表现新疆的山川形势、政区建置、台站体系和民俗特色,反映出清朝对其军事控制和行政管辖。从嘉庆朝开始“新疆”取代“西域”成为多数新疆地图的地域称谓。总体而言,清中期新疆地图的精度超越宋明西域地图,表现了清朝对新疆管辖的深化和对地理认识水平的提高。
清朝中期地方官员和学者所绘的新疆地图往往都采用传统形象绘法,在地名注记上也开始重新标绘考证汉唐西域地名,而且往往有大量的文字题记、注记。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甘肃知县明福于乾隆中后期所绘《西域图册》中的《西域总图》有大量的文字注记说明图中所绘内容,分图中还有描绘风俗的内容;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疆图说》也采用一图一说的形式,用大量图说文字注明新疆各地的距离。又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嘉庆《伊犁总统图说》中的《新疆总图》中往往在清代地名下标注“古某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咸丰《新疆总图》中也在图左上方标注古地名,使得中原的读书人能够将图中所绘之地与传统史志记载建立对应关系,从而形象而直观地了解新疆的时空变化与现实状况。
四、结语
汉唐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和地图的搜集、绘制与运用,留下了众多西域地图,直观反映了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和认知,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清代是新疆地图绘制和运用最为普遍的朝代,这与清代重新统一新疆、欧洲近代测绘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沙俄的东扩密切相关。清代的新疆地图主要分为康雍乾时期清廷采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皇舆全图”系列舆图、准噶尔汗国受清朝和沙俄双重影响绘制的“准噶尔汗国图”、清朝官员学者采用中国传统绘图方式绘制的新疆地图集等三种类型,分别表现了三种不同的西域观和新疆观。
康乾时期统一新疆,实现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的全面管辖,清廷动用国家力量、引进西方近代测绘技术测绘西域,表现了清代新疆的现实情形。而《乾隆内府舆图》还通过标绘新建汉语政区城池、描绘广义西域等地图话语,彰显了乾隆帝统一新疆的文治武功,表达了清廷教化“番夷”“天下一统”的王朝西域观和疆域观。
雍正、乾隆年间,受清朝大测绘的影响以及与俄罗斯和清朝划界的需要,准噶尔汗国绘制托忒蒙文《准噶尔汗国图》,反映了准噶尔汗国以西域为中心的疆域观和民族观,也表现了近代疆域领土观念在游牧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
清中期以来,在清王朝全面管辖新疆的基础上,清朝官员和学者开始采用中国传统绘法编绘新疆图籍。除了单幅地图之外,《西域图志》《新疆图说》等成套的新疆政区地图集和新疆历史地图集大量出现,将新疆清代地名与汉唐西域地名融为一体,突出新疆的台站体系和新建政区,从而反映了清朝对新疆管辖和认识的深化。